妈妈教我当医生
妈妈教我当医生
(编者按:我院消化内科创始人黄宗心教授,因病久治无效,于2010年8月20日下午3时与世长辞,享年88岁。在黄宗心教授追悼会之后,编者曾约黄教授的二女儿蒋本瑜写一篇缅怀母亲的文章。蒋本瑜的文章已在网站发表,现将其刊登,以示对黄教授的纪念。蒋本瑜是原西安医科大学77(5)级学生,1982年本科毕业后,攻读我院超声医学研究室张爱宏教授的研究生。现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医学院从事超声诊断工作。本文摘自http://775forever.blog.sohu.com)
妈妈教我当医生
蒋本瑜
今天是教师节,也是妈妈离开我们三周的日子。在过去的20天里,坐在越洋飞机上无法入眠的时候,在我和亲朋好友一起回忆的时候,妈妈的音容笑貌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动,一件件尘封的往事一下子鲜活起来,我想把它们写下来,会更好地寄托我的哀思。
人们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我的妈妈是我终生的老师,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不仅仅因为她是西安医大的内科教授,我曾西安医大的学生。更是她把我领进医学的大门,是她把着手教我当医生。
我曾写过博客称我的学医之路始于南岔—那个我插队的小山村,也缘于我有个当医生的妈妈。十七岁那年上山下乡的大潮裹挟着,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农村,不同的是我的背囊里多了一些药棉,红汞和常用药品,一本妈妈特意买的《赤脚医生手册》。在那缺医少药的村子里,凭着在学校里会包个伤口,点个眼药的本事,也算个小大夫吧。在每次回西安的日子里,妈妈把我带到医院里跟护士学打针,到中医科学针灸。回乡后根据妈妈教的许多基本医学常识,如无菌观念,避免胸腹部危险区等等,大胆谨慎的实践,深得社员和同学的好评,后来又有机会到坪头卫校去学习三个月,成了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从那时起我就渴望能有机会上医学院深造,在近十年里,我心里一直在呼唤着‘我要上学’,这是我在小学一年级时妈妈为我读过的《高玉宝》中的一段;但是我也很清楚,在当时,上大学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好比痴人说梦。
直到1977年冬天,这个梦终于实现了。那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我们姊妹仨一起被录取了,姐姐妹妹进了交大,我如愿以偿地上了西安医学院。记得那年的春节,一反往年的沉闷,家里显得格外热闹兴奋——大学的大门终于向我们打开了。到西安医学院(注:即现西安交大医学院)报到好像是在3月初,妈妈执意要送我去上学。那时我早已不是小孩子,走南闯北的去过许多地方,到南郊的小寨还用人送吗?妈妈说“这是不一样的。”寥寥几个字,我当然读得懂妈妈的心。上大学对我对她,都可谓是个里程碑的吧。记得那天下午妈妈要去上海探望病重的外公外婆,一早我们就直奔小寨,换了两趟公共汽车来到医学院。由于我们到得太早,新生报到处尚未开门,学生处工作的老师也曾是妈妈的学生,寒暄了几句就开始办公,于是我成了77级的第一个报到的新生,我的学号是775001。
在医学院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在中断十年后重返课堂,我和同学的学习劲头之大,用疯狂来形容也不为过。我则更为在课堂上听到那些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术语和病名,从理论层面上真正理解它们而兴奋不已。每每周末回家,就拉着妈妈说个不停。入学的第一学期,我们还在上基础课,我奶奶已是肺癌晚期。一天妈妈对我说,奶奶是中心性肺癌,完全肺不张。然后她就让我在奶奶身上学习物理诊断的方法。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那个老旧的沙发上端坐着微喘的奶奶,妈妈的左手置于奶奶呈桶状的胸部,右手中指一遍遍叩击着左手指,‘注意这是实音’ 我学着双手放在奶奶的胸部,反复体会着语颤增强的肺实变体征,叩诊,听诊……。我想这是一堂绝无仅有的物理诊断学课,只有一个学生,老师是妈妈,病人是奶奶……。医学是实践科学,妈妈总是抓住一切可能为我创造实习的机会。家里的钟点工是风心病二尖瓣狭窄,妈妈让我仔细听听她的心脏杂音;老阿姨脾脏大,当她来家里看病时,不忘把我叫上。我在医院见习实习时,妈妈也会为我开点小灶,若有罕见体征的病人,我会得到消息,到病房去检查病人。由于妈妈的影响,我一直注重操作实践,基本功比较好,加上手脚利索,无论在那个医院,我的操作总能赢得称道。
妈妈待人谦和,慈善,尽管医术精湛,经验丰富,但医德高尚,关心病人,无论高官,还是农民,一视同仁,悉心诊治,从来不摆医生的架子。从小就看到好多邻居,直接间接生人熟人到我们家来找妈妈看病咨询,既有教授干部,也不乏普通教职员,还有不少是我家保姆的同乡朋友,妈妈总是耐心地听病人的讲述,认认真真给他们讲解。我往往在一旁一知半解地听着,看着妈妈如何接待病人。在70年代中期,《陕西日报》曾在头版登过一篇有关妈妈抢救一个停止呼吸心跳几分钟的农村大娘的事迹。那是我见过的老妈唯一被宣传的先进事迹。当时为了表示尊重知识分子的政治需要,陕报丁总编正好住院是妈妈的病人,立即抓住了这个典型。可是妈妈对这种政治拔高一点也不感兴趣,从来不听她提及。我当了医生后,在和妈妈的交流中,我清楚这不过是在她临床生涯中一个极为普通的病例,那靠的不是什么“思想” ,而是医生一份执着地坚持。当时社会上把听诊器方向盘尊为最吃香的职业,但是我们家好像一点也没沾到这个医生妈妈的好处,我和姐姐下乡去了宝鸡,招工在宝鸡当工人,妹妹按政策留城,去了个集体小厂。什么参军提干上大学,都与我们无缘。我想妈妈一定有许多有权力有办法的病人,只是她从来不向他们开口,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到二院工作后,同事们给我讲了一个在老职工里口口相传的故事,倒是描述了一个真实可爱的妈妈。当年消化内科病人极多,挂号室的工人把黄教授专家门诊的号留给对门卖肉的售货员,换了一块好肉;而黄教授排队拿肉票只买到一溜肚皮肉。我在做住院医生时,管着一个女病房,几个大妈大姐对身怀六甲,还要隔日值夜班的我很是关照。一天我问起婴儿棉裤的做法,大妈们让我买了布和棉花,剪的剪,缝的缝,半天就做好了两条小棉裤。待我回家得意把棉裤拿给妈妈看,她却一脸严肃,‘医生是不应当利用病人的,我连毛衣都不让病人打。
作为学生我聆听过妈妈的大课,参加过妈妈主持的全科病案讨论及无数次教学查房。也和其他同学一样为她条理清晰的讲解、论据充分的分析所折服,为她从容优雅的临床检查技术所倾倒。但作为女儿,我也清楚这些背后妈妈的付出。有一次下了一夜大雪,为了上大课,妈妈拄着拐杖,早上六点从家一直走到和平门,才坐上公交车到医院。当年除了交通不便,政治学习,下乡巡回医疗,加上繁重的临床工作,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早上见到妈妈仅仅可数的几次。妈妈一直对我讲,当了医生就得学习一辈子。家里订了多本医学期刊,记忆中在我4-5岁时,大概爸爸出差,我有幸和妈妈一起睡大床,就见过妈妈在睡前看这些杂志,一边看还一边告诉我一个人肚子里有几百条蛔虫(这大概是我最早的医学启蒙吧)。直到妈妈六十多岁时,她还在不断看期刊,我们常打趣地说“黄教授功成名就,还要看书吗?”妈妈对我说过,“每周查房,我都要讲一点新东西,不看书咋行”。记得内科二病区住过一个年青病人,间歇性腹部绞痛,发作起来惨叫声在病房里回荡,可是平时查体又没有体征,化验也大致正常。病人住了几周,会诊几次,还是下不了诊断,除了止痛,也无法治疗。后来妈妈从化验报告中找到血铅增高的蛛丝马迹,反复问诊,不断查资料,最后确诊。原来这年青人,由于从小患癫痫症,一直用中药治疗,造成铅中毒。经过驱铅治疗,很快痊愈。
我毕业后,妈妈很尊重我的意见,常常和我讨论。每当我回家,总和妈妈像普通母女一样聊天拉家常,只是我们谈的更多的是我遇到的病人的症状体征,是妈妈一个个亲身经历的临床病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故事。在她晚年,我每次回国,妈妈还要问问新技术,新疗法,并让我看整理的整整齐齐的《医学论坛报》。
妈妈就是榜样,就像润物无声的细雨,点点滴滴的影响着我,教我做人,做事,做学问,做医生。如今和妈妈已是天人两隔,再也没有向妈妈当面请教的机会了。正像我的发小所说,我身上流着妈妈的血液,我从事着妈妈穷其一生的事业,我是她生命的延续……不过我更想告诉妈妈,若有来世,让我们还做母女,再为师生。
上一篇: 想起白求恩
下一篇:我在耶鲁的日子里——耶鲁大学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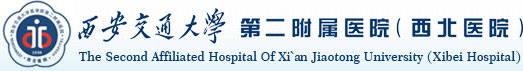





.jpg)
